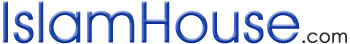እስልምና ኒ ምንታይ መርጽካ? {1}
እስልምና ኒ ምንታይ መርጽካ? {1}
伊斯兰历一四零九年(公元一九八九年)开斋节之后的第二天,我在公司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他希望我写一篇关于自己归信伊斯兰的心路历程。我想这项建议来得正是时候,我的确该为自己的信仰过程作一番回顾、记录,否则数年之后,说不定我连自己如何成为一个穆斯林的原因都会逐渐淡忘掉。纵使我明了自己是个毫无社会地位的小人物,而一篇自述性的文章更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但我还是祈求真主,赐我耐心与智能来完成它,并能激起穆斯林兄弟们少许的共鸣,以坚定我们的信仰。
任何一个归信伊斯兰的人,在谈起他们未成为穆斯林之前对伊斯兰的了解,总是千篇一律的说,回教就是可以娶四个老婆、不能吃猪肉的那种宗教。我亦不能免俗,我对伊斯兰的了解仅止于此。但是,更令自己惭愧的是,我毕业于阿拉伯语文系,在修习了四年阿拉伯文之后,竟然对伊斯兰的了解程度是“零”。甚至可以说,我了解的伊斯兰是被人有意、无意扭曲了的宗教。一九八五年我毕业之前,伊斯兰在我心中是个负面的宗教,因为我从非穆斯林处得到错误的资料,又接触了一些行为不检的穆斯林,伊斯兰并没有吸引我的成分。另外一方面,我是个有神论者,我不能确定当时的我是偏向一神论或多神论。反正是逢庙必拜,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情,蒙着头到处烧香礼佛。但是我心灵的最深处,确实认为这个宇宙有个主宰,只是从没有人告诉我如何去认识祂。
一九八五年九月中旬至一九八七年七月底我在部队服役,服役的第二年开始,我和一位伙伴吃素。吃素的原因非为宗教,只因我那位朋友不擅烹饪,我为了贪图小锅菜的美味,也觉得那些煮大锅菜的厨房实在很脏。很奇怪的是,我有几位吃素的朋友却会喝酒,而且平时谈吐亦粗俗不堪,和我们一些没有明确宗教信仰者无多大之区别,可以说区别只在饮食上罢了。当兵时我最厌恶的事,就是每次庆生会或聚会总是少不了酒,我厌恶酒简直到了极点。而每次参加亲友的婚礼最让我尴尬的总是有人强行劝酒喝酒。我心里常常幻想,如果我是个回教徒的话,就没有人会逼我喝酒了,但那也仅止于幻想。
在退伍的前两个月,我那位吃素的朋友邀我去他在的家,没想到他母亲竟帮我安排了一个十几个人欢迎的入教仪式,而我也在毫无招架能力下半推半就的入了一贯道。入他们的教倒也是无所谓,反正他们也是信仰神者。但偏偏他们还要我发了一个毒誓,意思是若是将来叛教的话,将遭天打雷劈、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一九八七年九月下旬我怀着兴奋、期待的心情前往梦想多时的沙特阿拉伯学习阿拉伯语。初到沙特,当地以宗教为生活重心的社会型态深深的吸引了我。我心里暗自的想,这个国家突然暴得的富庶,一定和她整个国家的人民虔诚的信仰有某种看不到的关系。虽然我心里如此的想,但是对于穆斯林一天五次的礼拜,我还是采取讪笑的态度。我心想,信仰虔诚也就够了,干嘛还得一天作五次礼拜?浪费时间、消耗人力、减少睡眠时间,简直没有经济效益嘛!可是渐渐地,我发现伊斯兰并不是我在国内所了解那种落后、浅薄的宗教。再加上经常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穆斯林,主动来向我介绍伊斯兰,有几次我冲动的想立刻宣布信仰伊斯兰,但我心里的障碍一直未克服。就是和我一同到沙特求学的同伴,原本在国内都是同学,我知道自己一旦入教,一定会招致他们奇异的眼光,甚至会惹来他们背后的嘲笑,入教的想法一闪及逝。
一九八八年一月下旬,我和四位同学加上一位泰国同学利用学校放寒假,作了一次到土耳其的长途巴士之旅。出发当天,这位泰国同学的同伴齐集到校门口为他送行,我初次感到穆斯林的兄弟之情。从沙特到土耳其是一段漫长之旅,我利用在车上的时间,不断地对我那位泰国同学提出问题,请他解释什么是伊斯兰。一直到今天,我都不明了当时为什么我会问那么多关于伊斯兰的问题,而他的解答仍不尽令我满意。
伊斯坦堡是个让我相当感动的城市,原因在于这城市中处处可见宏伟的清真寺,那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清真寺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我在泰国同学带领下冒称自己是穆斯林进入每一座清真寺参观,寺中那些穆斯林礼拜、静坐的安详态度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在苏尔坦·阿罕默德清真寺,泰国同学教我双掌合捧祈求真主,我暗自祈求真主开启我的心灵,我记得自己当时对真主说:“如果你是真正的主宰,就请你打开我的心吧!”坦白说,当时我所作的祈求就和以前在国内任何庙中所作的祈求无多大差异,但以前的祈求都是功名利禄之类的现实利益,而这次在清真寺中的祈求却是加上希望真主开启我的心灵,接受我成为一个穆斯林,尽管我对伊斯兰仍是似懂非懂。
结束旅行回到沙特之后,我就盘算着请沙籍朋友带我去办入教手续。有一位华裔沙籍的阿布都拉·阿济滋听到我想入教的风声,立刻飞奔到我房间。我把自己的意愿告诉了他,同时也告诉他,我对伊斯兰仍是一知半解。他说一切不急慢慢来,但他要我当着他的面先念了作证词“我作证: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真主使者”。于是他说从那天开始我就是穆斯林了,并问我每天清晨的礼拜起得了床吗?我答:“没问题!”心里却是一点把握也没有。感谢真主,不到几天的适应期,一天五次的礼拜成为我生活的一部份了。而事实上,我心里充满了问号及一丝恐惧,所谓一丝的恐惧,是指我曾经在入一贯道时发了不得叛教的毒誓,我担心自己是否会意外死亡,阿布都拉阿济滋要我别傻了。但另外一方面,我对伊斯兰有太多的疑问了,为什么不能吃猪肉?为什么一天有五次礼拜?为什么女人全身要裹得那么紧?为什么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我的问题太多了,有些沙特朋友甚至被我问得答不出话来,好友福阿德甚至为了我的问题上图书馆,又到文学院找院长求教。我喜欢自己的一项态度,就是我虽然对伊斯兰有许多疑问,但从不因这些一时解不开的问题而否定了伊斯兰所代表的真理。感谢真主,许多存在心里的问题,也都因为许许多多热心的穆斯林兄弟协助而逐渐明了。在此我要强调一点,交往信仰虔诚的穆斯林兄弟是再重要不过的事,唯有坚守教门的穆斯林兄弟才是值得我们完全信赖的朋友,并可作为我们进德修业的典范。
以上是我个人归信伊斯兰的背景,虽然到今天为止我入教不过一年又两个月,但伊斯兰给我带来极大的影响。不管是内在的思想,或是外在的行为,伊斯兰深深的嵌入我的生活之中。我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一条正道,尽管我的父亲曾经怀疑我是否“走火入魔”,因为封斋、礼拜、饮食等等限制是家人无法立即接受的。我的一位老师明白的告诉我,他不喜欢现在的我,因为他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处处受到宗教的“控制”,是不正常的现象。而我不知道一个人的生活若离开了伊斯兰,和禽兽还有多大的差距。人短短的一生中,若不去思考我们为谁而活?为何而活?是谁造化了宇宙万物等等切身问题,反而汲汲于钻营名利,如此浑沌的一生比那飞禽走兽也高级不到哪里去。
我想利用这篇拉杂文章的最后一个段落,陈述一点自己所看到存在于穆斯林的某些隐忧。我不说伊斯兰存在某些隐忧,因为伊斯兰永远不会有隐忧,它是真主尊座前完美的宗教,没有任何一个人破坏得了它。我们看不到伊斯兰有任何缺陷,却到处可见到有缺陷的穆斯林。如果读者认为我上面这句话过于夸张、言过其实,那是因为您昧着良心才会有这种感觉。首先,我们看到穆斯林人口结构老化现象。这几乎是可以令人笑掉大牙荒谬的事,穆斯林人口老化?那么年轻人都上哪儿去了?难道是老一辈的穆斯林都抱独身主义不成吗?答案是否定的。直接了当的说吧?年轻一辈的穆斯林已迷失了他们的信仰了,他们逐渐和“卡非尔”沦为一体了,他们所知的伊斯兰跟以前的我没什么两样,仅止于“不吃猪肉”。更令人担忧的是还有一些年轻“穆斯林”也学那梁山泊好汉“大块吃肉(荤腥不忌)、大碗喝酒”起来了。不要睁着眼精说瞎话,说那是没有的事,也不要自欺欺人,为什么每个“主麻日”清真寺里总是疏疏落落,而礼拜的外国穆斯林数目可能比我国穆斯林要多。而我们礼拜的穆斯林中又以中、老年人占多数。“主麻日”礼拜的时间不恰当固然是一个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多数的穆斯林拋弃了伊斯兰。
亲爱的穆斯林教胞们,如果您认为自己每天口颂心系“除真主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真主使者”,礼拜、封斋、天课、朝觐您也均一一实践了就保证进得了天堂吗?我不那么认为。我们是否耐心地规劝亲友坚守伊斯兰?我们是否真诚地向非穆斯林宣扬伊斯兰的真谛?我们是否勤于学习及力行伊斯兰的教法?亲爱的教胞们,请您们正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要再作表面功夫了,不要再报喜不报忧了。为伊斯兰工作绝不能沾惹上“名、利”这两个字,贪图今世名利者无异于在敲火狱之门。今天若是我们要让“挂名”的穆斯林回到伊斯兰的怀抱,就必须要有壮士断腕、从根做起的决心。而所谓扎根工作,就是强化青少年的伊斯兰教育。每年均有穆斯林青年赴笈中东国家大多数归国只不过是多了个会说阿拉伯文的中国人,对于伊斯兰却仍是“门外汉”。或者是相当了解伊斯兰,却没有对伊斯兰提供任何服务。也不见有人对这些归国学子作追踪调查,或者是运用他们的特长,光是任其投闲置散,这种恶性循环无怪乎青少年日复一日疏离教门。亲爱的“关心”伊斯兰的长辈们,难道您们对这些现象不负担任何责任吗?难道您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在“主麻日”做好交际应酬吗?难道您只希望别人在您面前毕恭毕敬,唯唯诺诺吗?难道您们不知道您们的行为举止也称不上能成为下一代的典范吗?
今天要让伊斯兰在复苏的力量,可说完全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但是他们到底有没有那份担负使命的力量?而长辈们到底有没有认真的培养年轻人?如果大家仍像过去的四十年因循苟且,你争我夺。我想借着这篇文章激起有心人士关心穆斯林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同时恳请教胞们支持所有为主道贡献棉薄心力的人以及他们的工作,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您以实际的行动参与。最后,我祈求真主赐福于伊斯兰及穆斯林,祈求真主让穆斯林从迷误中归回正道,祈求真主赐给我永远虔诚的信仰,阿米乃
亚瑟·郑(台湾)
 ርእ ካዓ ( 2 )
ርእ ካዓ ( 2 )